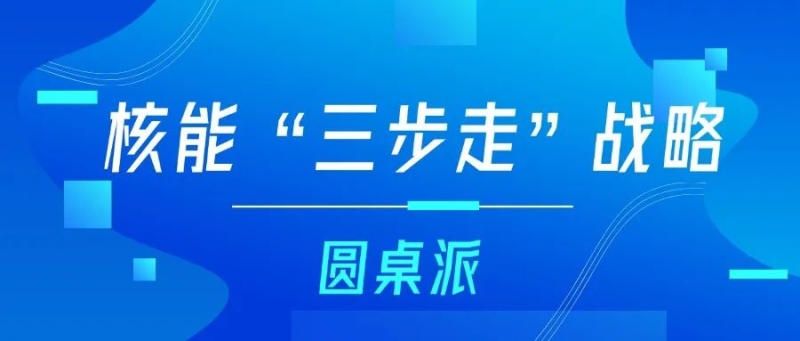编者按:
发展核能可有效促进我国新型能源体系构筑,保障能源安全、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热堆-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国在1983年提出的核能发展国家战略,其核心内容是解决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能源发展的新形势下,这一战略落实得如何?下一步将如何落实?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此刻——我国核能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中国核学会主办、中核集团承办的核能“三步走”院士论坛的举办将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关注燃到了”沸点“。本号从今日开设核能”三步走“战略圆桌派栏目,集纳各方观点,以期共启未来能源新纪元。
中核集团核能“三步走”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1983年1月12~18日,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召开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论证会”,经过对我国核电发展、国内外铀资源情况、国内后处理技术发展水平及后处理安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的充分论证,制定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首次提出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旨在逐步实现核能可持续发展和核燃料长期安全有效的供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热堆、快堆、聚变堆。热堆是核能发展的第一步,主要关注的是核裂变技术的成熟应用。热堆技术相对成熟,是当前核能发电的主要形式。快堆作为第二步,主要是采用快中子反应,能够实现核燃料的增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聚变堆是核能发展的最终目标。聚变能具有资源丰富,固有安全和环境友好等突出优势,是最终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历时40年发展,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热堆技术、快堆技术、聚变堆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推动我国核能工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核能发展处于最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热堆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发展
电力供应结构中比例逐步提升
我国热堆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适度发展、积极发展、安全高效发展和积极安全有序发展共五个阶段,现已跻身世界三代/四代核电技术前列。
起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采用“自主化”与“引进再消化”两条路径并行。期间,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成功建设,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使我国成为能够自行设计、建造、运行、管理核电站的国家之一;秦山二期60万千瓦工程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自主管理的大型商用核电站,为我国自主建设百万千瓦机组打下了扎实基础,走出了核电国产化的道路。
适度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采用“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引进技术、推进国产”的发展方针。先后又启动了四个项目(秦山第二核电厂、广东岭澳核电厂、秦山第三核电厂和江苏田湾核电厂)共8台机组的建设,装机容量660万千瓦,把核电发展推上了一个小批量建设的新台阶。
积极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0年)采用“招标引进、发展三代、一步到位、跨越发展”的核电建设道路。通过公开招标,国家最终做出了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和法国EPR技术的决定,并开工建设4台AP1000机组和2台EPR机组,作为自主化依托项目,开启三代核电技术自主化进程。在此阶段,累计30台机组开工建设,进入批量化发展阶段。在此期间,我国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明确了核电发展坚持“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路线。
安全高效发展阶段(2010年至2020年)实现了由“二代”向“三代”技术跨越。我国将“大型先进压水堆与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广泛吸纳国内各方面优势力量开展核电设计、装备制造、材料研制、工程技术等关键问题攻关。全面掌握三代非能动核电技术,在自主研发的ACP1000和ACPR1000机型的基础上,研发出满足当今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的“华龙一号”技术,形成型谱化系列化发展的良好局面。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新阶段(2020年至今)实现由“三代”核电向“四代”核电迈进。核电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成功并网,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商运投产,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核电机组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数为54台,总装机容量为5676万千瓦,商运核电规模全球第三,在建核电机组33台,总装机容量3883万千瓦,在建机组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022年度,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占全国电力装机总量的2.2%,核能发电量为4177.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5%,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7%。40年来,我国核电发电量持续增长,为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降碳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
快堆核能系统高效有序推进
已进入示范规模初期阶段
快堆核能系统是核能“三步走”发展的第二步,按快堆核能系统发展规律,快堆核能系统要经历“两循环、三阶段”发展,“两循环”指MOX燃料型快堆核能系统和金属燃料型快堆核能系统,“三阶段”指实验规模、示范规模和工业规模。
快堆是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钠冷快堆是技术最成熟的快堆堆型。经过70多年的发展,快堆技术日趋成熟,已经成为先进反应堆技术的典型代表,是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正处于示范堆向商用堆过渡的重要阶段。目前,全球已经累计建成30余座快堆,累计超过500堆年的运行经验,俄罗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正在积极开发和部署新一代快堆,全球快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正迎来新一轮重要机遇。从堆型来看,钠冷快堆发展已超过半个世纪,俄罗斯、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共建成过不同功率的大小快堆近21座,目前有5座快堆在运,分别是俄罗斯BOR-60、BN-600、BN-800反应堆、印度实验快堆、日本常阳堆。此外,俄罗斯已解决钠冷快堆大部分工程和运行问题,是掌握最有潜力大规模应用快堆堆型的国家。在燃料循环方面,国际上热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已经成熟并已商业化,美国和俄罗斯在快堆乏燃料后处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日本等国已掌握MOX燃料制造技术,美国已掌握快堆金属燃料制造技术。
我国快堆技术不断成熟。我国快堆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近60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掌握了大型钠冷快堆的工艺技术、工程设计、关键设备研制、建造、调试和运行技术。在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的支持下,中国实验快堆工程项目于2000年开工建造,2010年7月实现首次临界,2011年7月实现并网发电,建成了以热功率为65MW、电功率为20MW中国实验快堆,为快堆电站的设计、建造、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外,我国建成了约20台套实验装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研技术体系。目前,我国已掌握了钠冷快堆设计、建造、运行的关键技术,培养了一大批快堆专业技术人才,建设了较为完善的快堆产业链,为我国快堆商业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核燃料闭式循环体系已基本建成。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同步开发后处理技术,其分离工艺技术水平与当时的国际水平相当,现已有一定的基础。中试厂1993年完成了初步设计,主工艺流程采用PUREX流程。中试厂建成投运打通了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验证了主要工艺设备、检修设备及仪器仪表的实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支撑了后续工程建设,为我国后处理事业奠定了基础。燃料元件方面,我国已基本掌握MOX燃料设计和制造技术,初步具备辐照及辐照后检验能力。此外,我国积极推进金属燃料组件的科研工作。
聚变研究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国际磁约束受控核聚变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研究进程中,也先后探索了箍缩、磁镜、仿星器、托卡马克等众多途径,目标都围绕如何提高等离子体的关键参数,最终满足受控核聚变反应的条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托卡马克途径逐渐显示出独特优势,成为磁约束核聚变研究的主流途径。国际上自托卡马克开展实验以来,等离子体综合参数不断提升,装置的离子温度、密度与能量约束时间“三乘积” 提升了几个数量级, 先后在欧洲联合环JET与美国托卡马克聚变测试堆TFTR获得氘氚聚变功率输出,揭示了托卡马克磁约束可控核聚变路线的原理可行性。国际聚变界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使得人们对可控核聚变科学的认知愈加清晰,同时聚变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实现可控核聚变应用,诸多关键技术仍存在很大挑战,需凝聚全世界之力共同攻克。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努力, 建造一座核聚变反应堆,验证聚变堆科学和工程技术可行性。ITER的设计建造标志着国际可控核聚变研发正在由科学研究迈入聚变堆工程阶段。
我国聚变技术快速发展,已步入国际第一方阵。我国在1984年建成了核聚变领域第一座大科学装置 ——中国环流一号(HL-1)托卡马克装置, 实现了我国核聚变研究从原理探索到中大规模装置实验的跨越。HL-1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运行聚变装置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丰富经验。从此,中国磁约束聚变一步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2002年我国建成第一个具有偏滤器位形的托卡马克装置中国环流二号(HL-2);2006年,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东方超环(EAST)首次放电成功。2020年,国内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强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HL-3)首次放电成功。中国环流三号等离子体体积是国内现有最大装置的2倍以上,等离子体电流最高可达300万安培,等离子体离子温度最高可达1.5亿度以上,聚变三乘积可达1021 m-3·keV·s量级,规模能力仅次于现役的欧洲联合环JET(2023年底宣布退役)、日本JT-60SA(无氘氚运行计划)和ITER(计划2037年氘氚运行),预计2030前HL-3将是国际上唯一具备开展燃烧等离子体研究能力的大科学实验平台。近十年来,国内高校也建造运行一批聚变实验研究装置(如华中科技大学的J-TEXT、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KTX、清华大学的SUNIST等),这些装置在聚变基础问题探索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可控核聚变装置运行不断取得突破。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环流二号(HL-2)在国内首次实现归一化比压大于3的高比压运行,东方超环(EAST)首次实现403秒的长时间高约束模运行。国内当前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HL-3)实现100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高约束模运行,再次刷新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运行纪录,标志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向高性能聚变等离子体运行迈出重要一步。2023年,HL-3正式成为继欧洲联合环(JET)之后,全球第二个ITER签约卫星装置。同时,我国聚变堆关键技术研发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驱动聚变堆“点火”的外部加热技术方面,我国研发的射频负离子源中性束实现单级加速电压超160KV,平均束流密超270A/m2,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在聚变堆涉核关键技术方面,我国多项核心技术持续领跑ITER各方。我国负责的ITER产氚包层(TBM)系统率先通过了ITER设计评审,制造出全球首个全尺寸聚变堆产氚包层模块,率先完成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全尺寸原型件认证,发布全球首项核聚变领域国际标准《核聚变堆高温承压部件的热氦检漏方法》,实现了我国可控核聚变标准历史性突破。2023年,中核集团牵头实施的ITER托卡马克主机安装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TAC1安装标段工程,是ITER实验堆托卡马克装置最重要的核心设备安装工程,也是ITER迄今为止金额最大合同工程。这是中国核能单位首次以工程总承包形式成功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商业项目,也是中核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又一次坚定落实,意味着在核聚变领域,中核集团30多年不间断进行核电建设所形成的工程总承包能力获国际核能高端市场认可,将为我国深度参与聚变国际合作、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聚变堆奠定坚实基础。
擘画核能“三步走”发展新篇章
核能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兑现减排承诺的支撑,是非化石能源的主力,是实现“双碳”目标现实理性的选择。核电运行稳定,换料周期长,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的基荷电源,也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少的电源,在清洁替代和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转型中具有突出的优势。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科学安全有序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离不开核能。当前阶段,要按照“走稳热堆、走实快堆、走好聚变堆”的发展原则,加快推动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实施。
走稳热堆。我国热堆核能技术成熟,经济性和安全性好,装机规模、建造能力、运行业绩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要持续推进“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优化及后续机型研发,开展新机型经济性优化、非能动+能动安全系统设计、环境友好性提升、智能运维等技术研究,不断提升大型压水堆核能安全性与经济性,热堆仍是当今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实现核电大规模发展的主力堆型和主导产业。
走实快堆。研发和部署快堆核能系统不仅可以大幅提高铀资源利用率,将人类利用核能的时间从上百年延长至数千年,还可以实现放射性废物的最小化,要加快推进快堆核能系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早具备工程化建设的条件,尽早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是实现核燃料安全长期有效供应和核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走好聚变堆。聚变能源燃料储存丰富、固有安全性好、能效高,被认为是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选项。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强化聚变研发基地、平台、基础设施等资源保障,重视开放交流合作,激发创新活力动力,扎实走好聚变堆发展关键第一步。
奋进新征程,要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加快推动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不断构建“双碳”目标实现的“核引擎”,推动核工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核工业强国。